王夫刚,诗人,1969年12月26日生于山东省五莲县。著有诗集《粥中的愤怒》《正午偏后》《斯世同怀》《山河仍在》《仿佛最好的诗篇已被别人写过》和诗文集《落日条款》《愿诗歌与我们的灵魂朝夕相遇》等,曾参加第19届青春诗会,获过齐鲁文学奖、华文青年诗人奖、柔刚诗歌奖和《十月》诗歌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首都师范大学2010—2011年度驻校诗人。
1
通常情况下,诗人谈论诗歌难免乏味和画蛇添足,但博闻强记而又风趣幽默的博尔赫斯先生允许例外。我的判断,可能基于个人的喜好,也可能基于一种已被广泛接受的事实——如果你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我的建议是,不妨去读一读《博尔赫斯谈话录》这本书,伟大的诗人向来如此,不止文本带给我们阅读的直接喜悦和深刻启迪,就连说话,都是文学史的一部分。这本书的编者、也是访问者之一巴恩斯通,在简短的序言中这样赞美了博尔赫斯:“他曾以令人异常敬佩的友情同别人交谈了一生”。博尔赫斯的坦率、睿智和温文尔雅,值得大多数同行再三学习——访问者奥克朗代尔问他青年时期喜欢读哪些书,这位昔日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回答说,他现在喜爱的书就是他从前喜爱的书,他自己一生读的书不多,大部分时间都在重读;面对读者的温和提问,他的高傲看起来则有点漫不经心:“当今使我感兴趣的作家多已故去”。这让那些喜欢接受电台记者采访并且热衷于罗列书单的“社会诗人”心生不爽,按照博尔赫斯的逻辑,向他人兜售的书单越长,被打脸的可能性就越大(亲爱的朋友,但愿你没有这个好为人师的习惯)。巴恩斯通担心自己不能清楚地记住博尔赫斯说过的话,博尔赫斯用哲学家斯威登堡的话安慰他:“上帝赋予我们大脑以便让我们具备遗忘的能力”。巴恩斯通坚信,这位语言大师在那些带着问题的同行和听众面前,用他的谈话创造了一份我们这个时代的公开约书,他的声音以一词等于宇宙,这个词的中心无所不在,无处为其边界,听过或者读过他的人们,终其一生都被他所影响。巴恩斯通献给博尔赫斯的褒奖有没有言过其实,中国文化的江湖应对一般是“各表一枝”或“见仁见智”,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会仅仅因为博尔赫斯的善解人意而徇私舞弊地做出上述断定。作为一个业余诗人(亲爱的朋友,不要向我打听谁是我们身边的专业诗人),我每天都不可避免地与古老而与时俱进的汉语发生或直接或隐形的关系,但汉语的“时代轻佻”和“社会僵化”同样无处不在地裹挟着我,勒令着我,让我心生羞愧,疲倦,继而充满深深的厌恶。我好像从来没有在汉语中遇见“他曾以令人异常敬佩的友情同别人交谈了一生”这种深情有趣的叙述、“上帝赋予我们大脑以便让我们具备遗忘的能力”这种深入浅出的教诲以及“福克兰群岛那档子事是两个秃头男人争夺一把梳子”这种惊世骇俗的隐喻(亲爱的朋友,这可是博尔赫斯被要求评论交战双方都跟他有关的一场血腥战争哪)。博尔赫斯不相信流派,不相信年表,不相信标明创作年代的作品,恐怕也不相信我的粥中愤怒和泥淖深处的绝望:我对世界的爱和理解远远不够,居然担心最好的诗篇已被别人写过。
2
博尔赫斯曾谦逊地说,他的一生是一部错误的百科全书,一座博物馆,和他同时代的诗人、作家米沃什也曾殊途同归地面临这种无法取消的设问:“我读过很多书,但把那些书一本本叠起来,然后站在上面,并不能增加我的高度。”很多中国读者认为,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米沃什的社会影响力甚于博尔赫斯,因为他没有像博尔赫斯那样与中国人最为津津乐道的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如此简单粗暴地比较两位宗师级别的文学人物显然不够合理——问题在于,合理不合理在中国读者这里自有一套体系,这个体系的标准,既不是美洲的博尔赫斯说了算,也不掌握在欧洲的米沃什手中。我很庆幸我对博尔赫斯和米沃什的热爱或者有限理解不存在两者选一的困境,我乐见我的阅读在他们巨大的沉静的文学阴影中旁观乃至享用了清晰的光辉。米沃什说,他勇敢而大胆地确信他有重要的话要对这个世界说,但在同一篇文章中又告诉我们,他写过各种题材,并且大部分非己所愿。这有点像他自我选择的流亡生涯,世人只见他轻描淡写地说“一个孤独的人,过着隐居的生活”,却往往忽略了后面还有一句:“流亡是一切不幸中最不幸的事,我简直坠入了深渊。”米沃什作品的中文译者、诗人张曙光认为,米沃什在诗中呈现的情感和经验复杂而深邃,他相信语言的力量并力图通过语言来拯救时间和随时间逝去的一切,而不仅仅是客观记录历史;另一位译者、诗人西川谈到米沃什晚年早期的短诗《礼物》时说,米沃什已经将记忆和痛苦安排妥当,他惯用的雄辩的武器似已收仓入库,西川同时断言,任何一种观点都有可能导致米沃什缩水。米沃什是用来阅读的,也是用来研究的,但归根结底是用来阅读的——即便如此,如我这般试图用几百字来谈论米沃什,不仅力不从心,而且不够道德——那么,就让我们再次从简短的阅读开始,向这位年逾九旬依然写作到深夜的诗人致敬吧:“在我生命的第九个十年,我内心涌起的感觉是可怜、无用。一大群人,无数的面孔,形状,某些人的命运,某种从内部与他们的汇合,但是同时,我意识到我再也找不到办法在我的诗中为我的这些客人提供一个栖身之所,因为已经太晚了。我还想到,要是我可以重新来过,我的每一首诗都将是某个人的一个传记或一幅画像,或者,事实上是对他或她的命运的一次哀悼。”这篇文字的题目叫做《可怜》,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读到的上面这段引文,已经是这篇文字的全部,如果我们没有为之意会,释然,久久思索,我们就有可能不是米沃什的“我的这些客人”,更配不上米沃什的“对他或她的命运的一次哀悼”。
3
布罗茨基毫不吝啬地称赞米沃什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或许是最伟大的。”而米沃什对布罗茨基的喜爱也从来没有顾忌他们显而易见的年龄差异,惺惺相惜的中国版本可以追溯到唐朝,发生在诗圣和诗仙之间的一段佳话。1964年,祖国的法庭以“社会寄生虫”的理由判处布罗茨基服苦役五年;1972年,更是剥夺国籍,以“欢迎离开”的方式驱逐出境。行前,布罗茨基给国家最高领导人写了一封信:“我相信我会归来,诗人永远会归来的,不是他本人归来,就是他的作品归来。”15年后,这位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兑现了他的预言,并以此安慰他所经历的审判、监禁、流放和海外流亡生涯。跟终老晚年的博尔赫斯和盛名归来的米沃什不同,早逝的布罗茨基去国后再也没有踏上故土,就连他的死亡也长着一张喜欢开玩笑的面孔,其跌宕起伏的人生堪称传奇大片。他的作品刚好相反,声音安静,风格多样,意象海阔天空,醉心于细节,醉心于具体描写,醉心于名词,醉心于发现,注重处理熟悉的事物和它们的微妙关系,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之间取得了难得的平衡。布罗茨基的写作缺乏大惊小怪和多愁善感,但预设了阅读的陷阱,粗心的读者往往把他归类为“一首诗诗人”(譬如《黑马》),甚至是“一句诗诗人”(譬如“它来到我们中间寻找骑手”),这种“量身定制”的取舍尤其符合中国读者所继承的“诗以言志”的古老责任。不过这并非布罗茨基的过错,他也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每一位读者寻找并发现他在作品中隐匿的谜底和“原来如此”的命运,尽管他并不信赖瞻望——在《小于一》中他说过,“回顾比其相反更有益,明天就是不如昨天有吸引力。”布罗茨基的作品像坐标一样检验普通写作者的文字含金量——如果我们感受不一,判断迥异,也不必展开辩论,就像此刻,我在文字中一厢情愿地惊动博尔赫斯、米沃什和布罗茨基出场,不是绑架他们证明我的诗歌抱负,只不过通过他们分享诗歌所产生的乐趣、美德和荣誉而已。我们也许活得不够好,也许写得不够好,但“活得不够好”和“写得不够好”并非从属关系而是并列的存在,换言之,“活得足够好”亦非“写得足够好”的前提或者保障。我们需要生活而不是生活的比较学,需要诗歌而不是诗歌的落日条款跟瞻前顾后的欲望沆瀣一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人微言轻,要想言简意赅地讲述自己的立场并且获得普遍理解,求助于名人支持便成为一种肉眼可见的捷径——喜欢长期住在阁楼里的哲学家齐奥朗曾告诫说:“我既没有愁苦到足以成为诗人,又没有冷漠到像个哲学家,但我清醒到足以成为一个废人。”而博尔赫斯则对他信任的巴恩斯通有过类似的提醒:“唯有个人的问题才有意思,别提什么共和国的未来、美洲的未来、宇宙的未来,那些东西毫无意义。”
(选自《草堂》诗刊2021年10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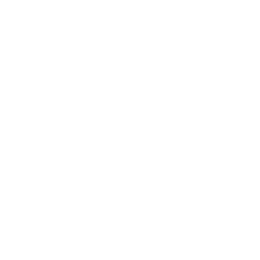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
官方微博
 官方抖音
官方抖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