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持续践行“课堂有识、课外有趣、成长有爱”的创意写作育人理念,2025年6月,创意写作学院“诗韵齐鲁”诗词研学第四期如期而至。本次研学由孙秀芳老师带队,深入“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的故居,旨在引导学生在文学的原生场域中,完成一次与经典对话、与现实交织的深度写作实践。

砚明,本名宋建,大写意画家、泰山雅趣斋主人,师从秦龙先生、近僧先生。曾任中国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国韵文华书画院展务部主任、《美术展览》杂志编辑。现为国韵文华书画院特聘画家、湖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泰安市美术家协会会员、“传颂演艺”发起人。作品多次入选国级展览,包括“中国画名家四条屏作品展”、“丹青名家楹联特展”、“国韵文华书画院第一届年展”、“中国色彩—系列活动”等。

唐僧,本名李鑫,泰山石专家、诗人,投身于泰山石收藏与研究,偶尔与朋友谈诗论道,对诗歌、小说等有深刻的思考,见解独到,半隐于市。

孙秀芳,笔名孙洛,作家、诗人,祖籍山东,生于吉林,中国作协会员。本科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公共关系学专业,研究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专业,小说发表于《中国校园文学》、《微型小说月报》等刊物,诗歌入选《万物的叶尖:中国创意写作2022》,出版有非虚构作品《企业家的黑天鹅》等。
2025年10月19日,创意写作学院教师孙秀芳带学生赴淄博开展“诗韵齐鲁”第四期研学活动。本次活动以“走进‘聊斋’,在蒲松龄故居叩问人心”为主题,通过走进蒲松龄故居,体会《聊斋志异》诞生的情景,形成“走入—感悟—实践”的学习链路。

一、故居寻踪:在“聊斋”里与蒲松龄先生对话

队伍静静地走入那座典型的北方农家院落——蒲松龄故居。青砖斑驳,蔓草微曳,岁月的痕迹触手可及。孙秀芳老师并未急于讲解,而是让同学们先自由感受,她轻声布置了首个任务:“寻找一个最打动你的物象,它或许是一件实物,或许是一种氛围,并思考它为何能穿越三百年,依然保有打动你的力量。”

冯欣欣在蒲松龄设馆授徒的“振衣阁”前驻足良久,她在随后的分享中说:“站在这儿,我好像能看见那些渴望知识的年轻面孔,也能感受到蒲松龄在清贫中坚守书桌的那份孤寂与丰盈。

”张佳铭则对那方著名的“聊斋”石刻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注意到石面被岁月磨得光滑,感叹道:“‘聊斋’这两个字,仿佛不是刻在石头上,而是被一代代读者的目光抚摸出来的。”

在“柳泉”旁,王致远俯身观察泉水的清冽,在笔记里写道:“蒲松龄在这里听南来北往的故事,就像这泉水,看似平静,底下却涌动着无数人生的悲欢离合。所谓创作,或许就是打捞起这些沉在底部的闪光碎片。”

这些零散却真切的初感,成为了后续写作最原始的素材。
二、落笔成文:感悟后在本上画出痕迹
参观结束后,学生们带着被激发的灵感与思考,分散在故居的各个角落,进行自由采风与初步创作。经过沉浸式的观察与思考,他们的笔触显然更具个人色彩和探索意识。

赵鑫朔试图将泰山石的“厚重”与狐仙的“灵动”并置,他写道:“我想象一方泰山石上,依偎着一只白狐。石是沉默的誓言,狐是流转的情愫。它们对峙千年,共同守护着一个关于永恒与瞬间的秘密。”他还向大家展示了当时创作的另一首诗《落红》:“阅过春的暖/走过夏的繁/醉过秋的清/熬过冬的寒/风吻枝头/便漾开花开的温柔//时光回眸/又低吟花落的清愁/那一寸春泥里/终究藏了多少/花的泪、未了的忧。“孙老师说这像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现代诗版本,并让他读读洛夫的诗。

张宇宣则受魔幻现实主义讨论的启发,尝试用现代视角改写聊斋故事:“她不是一个传统的狐仙,她可能出现在今天的地铁站,穿着一身不合时宜的白衣,对每一个看她的人说:‘我丢了一颗心,你见过吗?’”
冯欣欣的笔记更加片段化,充满诗意:“青苔/爬上石阶/想要倾听/那些被遗忘的对话//而月亮/还是三百年前的月亮/静静照着/旧书斋里/新写下的断章。”
这些文字或许尚显青涩,但已能看出他们在努力消化文化养分,并将其转化为独特的文学表达。孙秀芳老师在指导时强调:“不必追求立时写出完美的作品,最重要的是保持此刻的敏锐与真诚,让感受与思考自然流淌。”
三、三师沙龙:从“聊斋”、魔幻现实主义到诗歌创作
午后,研学队伍来到“为一书院”,围坐举行“三师文学沙龙”。孙秀芳主持,和砚明、唐僧两位老师,及同学们围绕“诗歌写作、《聊斋志异》与魔幻现实主义、泰山石文化”等话题,展开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对话。

沙龙伊始,孙秀芳老师从诗歌意象的营造谈起。她以蒲松龄笔下的“狐”为例,说:“诗歌与聊斋,都在追求一种‘熟悉的陌生感’。狐仙鬼魅,本质是高度意象化的人。写诗,也要找到那个能承载复杂情感的‘狐’,让抽象的意念获得具象的形体。”她鼓励学生尝试“意象置换”练习,将现代情感装入古典意象,或为日常事物赋予神异色彩。
话题自然引向《聊斋志异》与魔幻现实主义。唐僧老师对此颇有研究,他指出:“很多人将蒲松龄称为中国的马尔克斯,这其实是一种误读。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源于其独特的历史与地理环境,是‘真实的魔幻’;而聊斋的狐鬼世界,根植于中国深厚的志怪传统与儒家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曲折批判,是‘魔幻的真实’。蒲公写官场,便用‘冥府’;写爱情,便用‘狐女’,他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象征系统来隐喻现实。”他启发学生,在创作中不应简单模仿怪力乱神,而应学习这种“隐喻性写作”,将个人的观察与思考,通过一个独创的象征系统表达出来。

砚明老师则将话题引向泰山石文化。他展示了几方泰山石的图片,石上纹理自然天成,似山水,似人物。“泰山石敢当,是镇宅辟邪的符号,这是石头被赋予的文化人格。这与聊斋中‘物皆有灵’的观念一脉相承。”他引导学生思考,“在我们当下的写作中,如何让一块石头、一棵树、一件老物件不再是无言的背景,而是成为有生命、有故事的角色?这是对作者想象力和文化积淀的双重考验。”
三位老师的观点相互激发,层层递进,从具体技法谈到文学观念,为学生们打开了一个立体的、富有深度的文学思考空间。学生们也加入到了热烈的讨论中,在自由提问环节,周海晨就“如何平衡虚构叙事中的‘奇’与‘真’”向唐僧老师请教;郭艺峰则对唐僧老师提出的“意象的现代转化”表现出浓厚兴趣。思想的火花在桌上不断迸溅。

这次研学,是“人文现场+作家指导+创意写作”三维教学模式的又一次深化。我们不仅带学生来到了蒲松龄故居这个文化现场,更通过三师沙龙,将现场的感性认知引向了理性的、多维度的思辨。学生们感受到的,不再是孤立的景点,而是一个立体的、可与当代写作观念对话的文学富矿。
供稿:创意写作学院
撰稿:赵雨辰、孙秀芳
摄影:赵鑫朔、张宇宣、张嘉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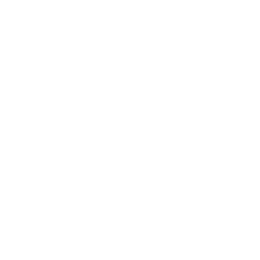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
官方微博
 官方抖音
官方抖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