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执浩,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汉诗》主编。主要作品有诗集《苦于赞美》《宽阔》《高原上的野花》等,另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随笔集多部。曾获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诗刊》年度陈子昂诗歌奖、鲁迅文学奖等奖项。

稍有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一首好诗的诞生过程是极为神秘的,写作者至多能说清楚这首诗“缘何而来”,但他可能永远也说不明白,这首诗“为什么是这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真正的好诗具有强大的自足性,通往真理而非道理。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落实到诗歌语境中,往往体现为,越是那些看似简易明晰的诗,越是经历了漫长而幽独的酝酿期,如同密封在坛子里的酒液,在时间内部缓慢地生长发育,不到开坛之日,你始终无法确认它是不是琼浆,为什么会成为琼浆。而一首平庸之作的出现,往往省略了这一鲜为人知的过程,它会轻易地露出马脚,它的来历和去向,不用作者自己现身说法,读者也能够猜出个大概来。或许正因为如此,很多优秀的写作者都拒绝一本正经地写所谓的“创作谈”,因为他心里比谁明白,无论自己怎样天花乱坠,口若悬河,而事实上,他是说不清楚的(就像我曾经在一首诗里写过的:“说不清白是命运/说清楚了是偶然”)。这种略显难堪的境遇,自然牵扯出了另外一个让我们百谈不厌的话题:究竟是我在写诗,还是诗在写我?若是前者,上述尴尬就应该不存在;但如果是后者呢?
我相信,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所说的第一句话一定是诗,或者肯定是,那种后来被我们称之为“诗”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惟有通过“诗”这种具有声音感的形式,才能有效地传递出人类的各种情绪:震惊、狂喜、忧惧、愤怒、疑虑、悲伤,乃至哑默……,诸如此类,不断涌现又消弭于无形的情绪,是诗让它们具备了便捷的释放通道,在放纵与约束之间获得了生命的平衡感;也惟有诗,才能呈示出人类——这个崭新的物种——初见这个奇异世界时,丰富、复杂而饱满的情感面貌,那是一种哑口无言,欲言又止,终至喋喋不休的强烈的表达欲。在嘈杂而激越的喧哗声中,诗的声音由最初的情绪表达逐渐转化成了后来情感表达,单音节的咏叹之音慢慢被拉长,变调,形成了多个转音,具有了节奏感和旋律,于是,便有了“歌”。从这种意义上来看,诗歌是“诗”的情绪或情感被一再拉抻之后的产物:“啊”被拉抻成了讶异、惊叹或称颂,“唉”被拉抻成了沮丧或哀怨,“哦”被拉抻成了顺服或回应……所有这些即兴的感叹,都将随着人类对陌生环境的适应和熟悉程度,逐渐转化成感怀,滋生成为某种越来越深沉、饱满,和具有普遍意义的情感经验,沉淀在人类的公共记忆中。
如果我们相信上述论断能够成立,那么,剩下的工作原本可以变得非常简单,即,我们只需尽最大努力将人类的那“第一句话”,准确地“复述”出来即可。但后来的事实却一再证明,这几乎不能算是一项工作,至少是无法完成的工作,因为我们谁也没有真正近距离地聆听过那句话。因此,我们关于“那句话”的所有复述,描述或转述,都不过是各种各样的个人幻觉而已。我们的每一次发声,都有可能会陷入自以为是的境地:你以为你听见了,而那其实不过是幻听;你以为你复述出来了,其实那只是你个人在表达。这种被动的局面几乎是每一位诗写者的宿命,从反抗,到接受,终至顺应,写作者只有通过不断地调整自我的心态和姿势,才能够培育出始终朝向澄澈、心无旁骛的定力。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能够通过上溯的方式,找到些许推动诗歌这种语言艺术经久不衰的动力源,譬如,人类历久弥新的那些情感,以及传导这些情感的材料;譬如,那种有能力一下子撕开眼前的现实雾障,并迅速唤醒我们内心世界的崭新语言。情感,材料,语言……,尽管这些东西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换,但总有一条牵逝的线路值得我们去探寻。而只有找到了这些东西,我们才能真正克服幻听和盲从,才能在面对最高的诗歌准则时,不至于失语。
从诗的缘起来寻找诗,好处在于,无论我们之间有多大的诗学分歧,最终还是能够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那就是:声音。把诗歌当作一种声音的产物,视“诗歌是一种声音”为谈论诗的前提,我们就可以相对容易地进入到诗歌的本体之中,以音色、音域、音高等元素来揭示和解读诗与诗、诗人与诗人之间的差异性和趋同性。不同的音色造就了不同的诗人,不同的音域让不同的诗都具足了各自存在的理由,不同的音高让诗歌作为一种公共情感的载体,发出了多声部的共鸣声。从声音角度去理解诗,也可以让诗摆脱文化意义上的皮相之争,进入到诗歌内部的肌理中,让我们有机会一窥诗学内部的结构、层次感,和某种古老而常新的秩序感。
可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是,每当我们沉浸在诗歌内部时,就会发现,真正的诗歌并不是诗人能够刻意书写出来的,至少它不是纯主观的产物。诗歌的现身往往肇始于现实生活对我们内心世界的挤压,但这种挤压何时能迎来喷薄之日,我们并无从把握。当一个写作者在产生了写诗的冲动时,诗歌其实已经先于冲动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了,他的感知系统已经隐隐约约触抚到了冰山一角。“我想写诗”,意味着,诗已经在那里了。但如何将虚有之“在”转化成实有之“在”,却是一道难题。表面上看来,此时,写作者只需要一个恰当的词语,或一个句子,来把那种情感的幻像勾勒出来,加以疏浚,充盈,然后用最精准的语言将之予以定型即可。可实际上,诗人只有在情绪最饱满的状态下,才有望接通外在物象所释放出来的电波,并由此构筑一个环闭的精神磁场。诗人在这里似乎变成了一首诗的通道,诗歌要通过他将幻象的情感,兑现成可以看见、听闻和感受的固态语言形式。至于说诗歌为什么恰恰选中了他而非别人,来作为自身的附体传导之物,同样也充满了神秘性。也就是说,当一首诗降临的时候,原本忧心忡忡甚或萎靡不振的诗人,会在瞬间被某种巨大的能量所激活,他将由上帝的弃儿变成上帝的宠儿:上帝给了他一个提示音,而一直警醒着的他正好听见了,又感受到这个声音召唤的力量。诗歌一定是写作者聆听某种召唤的结果——长时间地凝神定气,被破空而至的声音所吸附——接下来,诗人的工作就是要将这种召唤之音变成复活之声。诗歌的复活过程也是诗人对周遭世界的降噪过程,从这一刻起,他的心灵将服膺于这召唤之音的引导,他身心内部的所有通道都将全部为之打开,他一生积攒的词语将如宇宙陨石一般,携带着各种情感密码从他脑海中呼啸而过,诗人每一次看似漫不经意的攫取,其实都是对他内心修为的深刻考验,技巧,学识,情感的深度、浓度,以及人生的广度,等等,都将在写作的过程中纤毫毕现——这个过程其实是诗人献丑的过程,他不得不正视自己的缺陷和匮乏,并忠实于这样一种充满瑕疵的存在;当然,这一过程同样也是诗人彰显其才华和智慧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运气的成分将被彰显出来:那在书写中一次次看似偶然的词语选择,其实都是一种命数——一种成败在此一举的命数——它对应着写作者那一刻的心境、专业素养和注意力的集中程度。而这些因素,只有在事后,在一首诗真正结束之后,写作者才有顾盼和追思的可能性,但已然无可更改,即便有更改的可能性,也只是另一段心迹的展露,而无法还原初始的内心面貌。这样的结果是由声音的一次性特征所决定的,在此之后,所有的发声只能算是对前次发声的修补和调校。
发声学几乎是诗歌独具的一门学问,它直接指涉到了诗歌之所以是诗歌,这首诗为什么不同于那首诗,同样的诗写主题为什么效果迥异,等等,这样一系列有趣的问题。很多人能够清楚地说明格律诗的构成,从四言到五言,到七律,杂言,他们熟稔音韵学,古诗的平仄,调性,声律,甚至还能够老练地吟诵古诗词,但对现代诗却一头雾水满面茫然:这些松散的句式是诗么?如果是,它的诗意是如何形成和传导的呢?因为无从进入,因此终究无趣;因为感觉寡淡,所以干脆绕道而行……现代诗多年来就在这样的困境中转来转去,最终成了“诗人们自己的事情”。事实上,现代诗真的有那么神秘难解吗?在我看来,现代诗和古体诗一样,只是人类传递情感交流心灵的一种方式,类似于陌生人之间的“接头暗号”,有时甚至只是人群中的随意一瞥,或会心一笑,其中包含着一种人与人之间深层的信任关系,趣味,感应,或对人生志趣的共同理解,如同我们在嘈杂陌生的人潮中蓦然听见了自己的乡音,而随之在内心深处泛起的阵阵涟漪。一首优秀的现代诗肯定有其内在的节律和声韵,它的声音感由词语和贯穿在字里行间里的气韵来完成的,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咬合力,借助诗人自身充沛的气韵加以贯穿,每一次分行都是对气息的重新调整,以此形成了一首诗的基本面貌。不同的诗人以不同的声调来创作,不同的诗歌有着不同的声线和音域。我有一个不太确切却又固执的判断是,每一首诗在产生之前其实已经有了它自己的调性,问题在于,写作这首诗歌的人是否具有与之匹配的音高和音色。我们常说,应该多写那些能写之诗,而非那些想写之诗,这个说法有一个前提:写作者必须通过大量的长时间的尝试和训练,找到自己的音准,对自己独特的音色成竹在胸,并对自己的音高有一定的把握。蹩脚的写作者一定是一个五音不全的家伙,圆滑世故的写作者一定是一个擅长模仿他人的人,而自视过高的人常常会在写作中出现“破音”现象,至于那些惯于发“假声”的人,往往是虚情假意的写作者,除了炫技,别无所长……惟有自知之明的创造性的写作者,才能发出独特的声音来,这声音也许有如旷野独狼、井下之蛙、林间虫豸或云岭野风,这声音也许圆润,澄澈,也许古怪,令人不适,但必有其自身的来龙去脉。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声音,找准与自身气质匹配的发声方式,这是一个诗人写出属于自己的诗歌的一条秘径。
一首诗终止于最后落笔的那个词语(或标点符号),诗歌结束了,但诗人的工作永远没有完结之期。他再一次成了上帝的弃儿,他也将再次孤独地、耐心地等待着,再度成为上帝宠儿的那一天。诗人的命运如此奇异,玄妙莫测。所以,所有真正优秀的诗人每当夜深人静,都会扪心自问:我究竟写过什么?什么是我真正能写出来的?
(转自张执浩个人公众号“撞身取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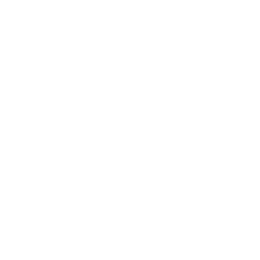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
官方微博
 官方抖音
官方抖音